导读
计划 系由公司运营,旨在将机器学习技术应用到音乐等艺术创作中的人工智能项目。6月 1日,公司发布了该计划运用人工智能系统成功谱写的,一段长达90秒的钢琴音乐,这成了人工智能涉足人类艺术创造领域里程碑式的一步。
然而站在19世纪末至今现当代音乐发展趋势角度看,人工智能所作音乐对于音乐史的价值究竟何在,以及未来这种“非人造”的音乐作品将趋向何种风格,都是值得作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本文中笔者将重点联系自身熟悉的西方现代音乐史、后现代文本学、艺术哲学等相关领域议题与视角,对此作一些纯个人层面的初步展望。
90秒的时长,在钢琴音乐史上,似乎还不足以撑起一首让人过耳不忘的不朽传世之作——最著名的可能只有肖邦( )脍炙人口的《“小狗”圆舞曲》(降D大调,作品64号之1);然而本月初,公司发布的这首90秒钢琴曲必将享受不朽的传世地位: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运用人工智能系统谱写的音乐。
它的诞生至少宣示着如下事实:基于海量经典音乐数据的摄入、消化和总结,计划所运用的人工智能已不满足于以往计算机自动作曲时对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既往音乐大师的纯粹风格模仿(那是计算机作曲干的活儿;据记载,在1987年,美国音乐家David Cope就已能运用他自己编写的作曲程序 in (Emmy),在一顿午饭时间内谱写5000多首巴赫风格的合唱音乐,并让人难辨真假),而是尝试主动创造曲式规则,并让自己拥有人类情感运作能力。
正是这一转向赋予了这首90秒钢琴曲星星之火般的特殊地位;而探究点燃今天这颗“火种”的“材质”和“火源”,却可以发现,这些促进人工智能作曲的动因延展得既深远,又耐人寻味:不但来自1950年代至今人类在计算机作曲领域的探索,更来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音乐在表现手法、创作理念上对上千年音乐传统的背叛与割裂,甚至在更遥远的时代也能找到其飘荡的因子——18世纪末,有作曲家(相传是海顿或莫扎特)发明了将几百个各异的小步舞曲段落列表,演奏时根据掷骰子加以对应、重组而生成的“随机音乐”;甚至公元前500多年的古希腊时代,将数字视为万物本源的毕达哥拉斯已经发现,音乐的声音体系与宇宙万物秩序一样,能够化为可数的整数(“音乐可数(四声)”)。
仰望星空,还需脚踏实地;同样,要展望人工智能作曲的未来,则有必要条分缕析探索一下,从计划中诞生的这颗火种,是怎样一步步被点燃的。
站在计算机“作曲家”前辈们宽厚的肩上
看曙光照临
1950年代,也就是电子计算机被发明并得到应用不到十年,就有人阴差阳错地开始吃起了计算机谱曲的“螃蟹”。
此人名列哈伦•希勒( ),美国人,23岁就拿到化学博士学位;1952年,时年28岁的希勒得天独厚地在伊利诺伊大学接触到第一台正式亮相于该校的冯•诺伊曼式计算机,目的是用其计算统计意义上理想聚合分子的大小。然而,身为乐迷的他在工作中“不务正业”地发现,如果将控制变量由几何数转换成音符,这些代码就完全可以用于谱曲,并符合对位法(在这种作曲法则中,相互独立的旋律得以同时融洽地发声)。这个发现让希勒大喜过望,他一发不可收拾地攻读起音乐学硕士学位,并利用计算机进行了一系列作曲技法实验。1957年,历史上第一支完全由计算机生成的音乐作品诞生,即弦乐四重奏《依利亚克组曲》( Suite);而化学家希勒也从此转行,从事计算机音乐创作。在转入音乐系任教,并成立实验性工作室后,他继续用计算机创作了《算法一、二、三》等乐曲。论及计算机作曲鼻祖,还得数这位完全出于兴趣转行而来的希勒。
列哈伦•希勒在他的音乐工作室里
希勒的“算法”音乐为这一科学与艺术跨界领域的后来者开启了先河。1980年代,执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艺术系的大卫•库佩(David Cope)从编写作曲程序出发,着迷于通过基于乐理的技法重组,来创造模拟不同过往音乐家风格的音乐。库佩认为,大多数经典曲作都是十二平均律音阶和对应的八度音阶的重组合,只要把握这个规律并以不断以巧妙的手法重新融合,就可以创造出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他开发的作曲软件 in (EMI)能通过特殊的匹配过程,分析并得出同一作曲家所有作品文本中的共性,并基于它们的出现频率赋予权值并保存。在计算机软件进行“创作”时,数据库中这些微小的共性特征得到与原曲充分同构的应用,从而使产出的作品具有十足“以假乱真”的效果,正如上文提到的“一饭5000首巴赫”就多次在实验中(与真正的巴赫作品一起用钢琴弹出)迷惑了听众。
进入21世纪,计算机作曲领域的研究更加步入纵深。一个典型例子是西班牙马拉加大学的超级计算机组群伊阿姆斯(Iamus),它的开发者将音乐的创造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相结合,并制定了一套程序。程序运行过程如下:电脑随机生成一些音符后,分析数据库中海量音乐作品并总结普适规律,并以这些规律筛选刚才生成的随机音符,被保留下来的进行两两“杂交”组合,再进行下一轮筛选,如此反复直到形成悦耳如作曲家原创的旋律。伊阿姆斯(Iamus)的“创作”奇迹般地通过了随后的计算机图灵测试——受测试者只有24%能从五个一分钟时长的音乐中正确分辨出伊阿姆斯(Iamus)的“作品”。
◆ ◆ ◆ ◆ ◆
从这些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出,写就第一首人工智能钢琴曲的计划并非凭空玄想,计算机作曲几乎从其自身诞生开始就与其相辅相成地发展着。不过,半个多世纪以来,运用日新月异的存储与计算能力,从海量数据化的经典音乐中提取、分析各类要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模拟式“创作”,是以往计算机作曲的主流范式;而眼下人工智能作曲不限于此,它将尝试在共情能力基础上主动发展新的作曲范式。
离开“调性”家园的现代音乐谱系
将添加新成员?
这种对范式的创新动力来自哪里?在笔者看来,除了创作载体发生革命性改变,人工智能追求对几十年来计算机作曲技法的新变与突破,并没有逃脱19世纪下半叶至今,西方现代音乐对作曲技法与音乐本体观念的革新传统。如果透过现代音乐发展史这一滤镜来观照,作曲技法革新的动力源至少要深深扎入瓦格纳( )乐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 und )前奏曲中,那个始终幽灵般浮游不定、得不到解决的主和弦:它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将西方音乐从几千年来追求和谐、优美与崇高的调性时代彻底撕裂;断裂的音乐大陆正向着20世纪漂移——柏林爱乐乐团现任音乐总监西蒙·拉特尔(Simon )称之为“(音乐)远离家园的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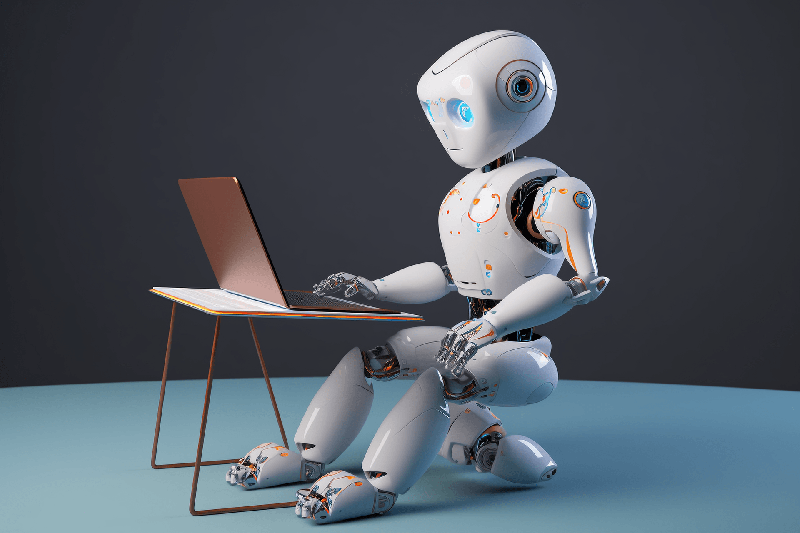
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
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活动,人工智能所产生的作品自然无法跳脱于音乐范畴;正因如此,在笔者看来,眼下如果我们为这一现象的出现而欢呼,那么我们更不该忘记应将其“作品”放入音乐长河,从音乐史的深远视角对其进行审视与展望。
西方音乐的断裂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事实上,尽管瓦格纳及其后的马勒( ,作有十部巨型交响曲,认为“音乐中应当包含全世界”)、德彪西( ,几乎推翻了所有传统形式,并以革命性的和声与色彩得到“音乐中的印象主义”之称)因为某些层面的激进技法,成了音乐史上的叛徒和革命者;但他们的创作,尤其是前二者,同时也将当时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浪漫主义抒情传统张扬到“滥情”的极致。盛极而衰,浪漫主义音乐从反对优美和谐的古典主义“套路”、张扬自我与主观情感出发,至此几乎耗尽了自我更新的全部能力,使得19世纪末立足于浪漫主义悬崖边的后人已再无前进一步的可能。
新变从体系内部悄然生发。除上述三者外,更多作曲家试图另辟蹊径。
斯克里亚宾( )试图将声音与色彩相联系;他试图将前人早有探讨但一直未有人付诸实践的音调与色彩系统性地联结起来。基于前人(18世纪德法两国科学家基歇尔与卡斯特尔)出版的音调光谱对应图,他将彩色灯泡与管风琴相连,演奏不同的音调时接通不同的彩灯。他特地将一行色彩谱标注在交响诗《普罗米修斯》总谱上,详细说明演奏时每一种声音用何种颜色相配。当“色彩风琴”演奏时,屏幕上各种与音乐相联系的色彩变幻莫测,此曲因此成为色彩音乐的名作。
一张斯克里亚宾唱片封面
斯特拉文斯基(Igor )被称为音乐上的毕加索,一生创作风格历经幅度巨大的三次改变。在这里特别有必要关注其第二次风格转变,即在一战后提出“回到巴赫”,风格由强烈蛮荒的原始表现主义转向愉悦得体的新古典主义——这一转向与当时欧洲音乐的总体转向相一致,是一种看似复古,实际上排斥主观浪漫情感、在以往古典形式“幌子”中试验各种前所未有的和声与色彩的“拟古”创作技法。
阿诺德·勋伯格(1874-1951)
勋伯格( )和韦伯恩(Anton )走得更远,其革新直接触及了作曲技法层面。在1911年出版的名著《和声学》中,勋伯格发明了用以作曲的十二音序列体系。采用这种序列体系谱写的音乐中,每一个乐句必须确保一个序列的十二个音都按固定次序出现,且每个音只能出现一次,如此排列组合构成全曲。这样的音乐从根本上排斥了调性,从而排斥了主观情感,成为一种完全基于数学运算的结构呈现;勋伯格的弟子韦伯恩继承了序列作曲法,并将其推向另一条道路,即融合各种乐器音色,并将这种试验推向极致的点描主义音乐。勋伯格在1921年自信地说:“我的发明将确保德国音乐在未来一个世纪内保持霸权地位。”此言不虚,二者对20世纪西方音乐影响巨大,斯特拉文斯基、梅西安、布列兹、施托克豪森等音乐家进行的自主创新都在此框架内运行;值得一提的是,序列作曲法还受到了1950年代结构主义思潮的关注,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认为,在这种严格受逻辑控制、音乐要素高度组织化的音乐样式中,“形式与内容有着同样的自然属性,均隶属于分析的范畴……内容从结构中获得真实性。”换句话说,当音乐结构本身成为内容的表达时,作曲家的主观感情表达实际上已被完全抽离于音乐形式之外。
长达一个多世纪且余波不断的浪漫主义音乐,经过瓦格纳、马勒、德彪西、斯克里亚宾等人在原有框架中的另辟蹊径,又经过简约主义、新古典主义等支流在各个层面上的革新试验淘洗,终于在20世纪勋伯格等人笔下,在作曲技法这一根本性层面得到了彻底的反转——这一反转,革的不止是浪漫主义音乐的命。
花如许篇幅梳理“后浪漫主义”的当代音乐发展史,并不是无用功。事实上,这一梳理至少向我们揭示了以下趋势:西方音乐在现代的发展过程,正是一个逐渐背离浪漫主义主情传统,驱逐作曲家主观情感,代之以关注音乐结构与技法的过程。正如上文中列维-施特劳斯所说,当形式和内容无分时,作曲已经成为了纯然算法和技术层面的游戏;而这一反转,恰好发生在电子计算机作曲初兴的时代。这意味着什么?
在笔者看来,这至少意味着以下判断:虽然艺术界比起科学界更倾向于对此持谨慎与高度保留态度,然而以技术试验维度为核心导向的计算机作曲及当下的人工智能音乐,其作品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游离于整体音乐史发展和流变趋势之外——人工智能谱写的音乐,和20世纪以来作曲家们在各个层面对浪漫主义的反叛和革新精神一脉相承,同属于一种抽离主观情感、将关注重心极度倾向于技术与结构层面的音乐创作。
◆ ◆ ◆ ◆ ◆
这个判断使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浮现:如果认同排斥、隐匿主观情感的“技术流”是当代音乐总体趋势——当作曲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时尚且如此——那么计算机以及人工智能音乐的创作,尽管目前看来以各种技术革新为导向,如果其内容表达长期停留在模仿并呈现人类各种主观情感的“悦耳好听”层面上,又会对音乐自身的发展产生多大意义?
到底需要什么?
再多一位悦耳的机器肖邦,还是……
事实上,这一质疑对人工智能作曲来说,首先将触及的是本体论意义的问题:它的诞生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什么用?或者更直截了当的问法:从60多年前希勒利用计算机代码“创作”音乐,到今天人工智能技术自行谱写音乐,这一切的意义,是仅仅在于探索数字技术在当下可抵达的边界,仅仅为了试验机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具备人的思维和情感,然后止步于此,还是在于另一个终极目的,即在未来某一天让数字技术取代有血有肉的人,来进行包括作曲在内的艺术创作?
囿于既有知识体系的局限,提出以上问题的笔者无法从人工智能专业视角出发进行探究并给出设想;仅立足于自身具备的人文主义知识背景“旁观“之,笔者更倾向于认同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它自身并不能成为其目的,更无法给出终极价值图景——换句话来说,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技术进步的一个面向,它的突飞猛进背后理当存在着某种为其提供终极价值的愿景。
这个愿景涵盖了什么?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将目光放得宽一些,看看人工智能在艺术创作外其他领域的发展,带给人哪些启示和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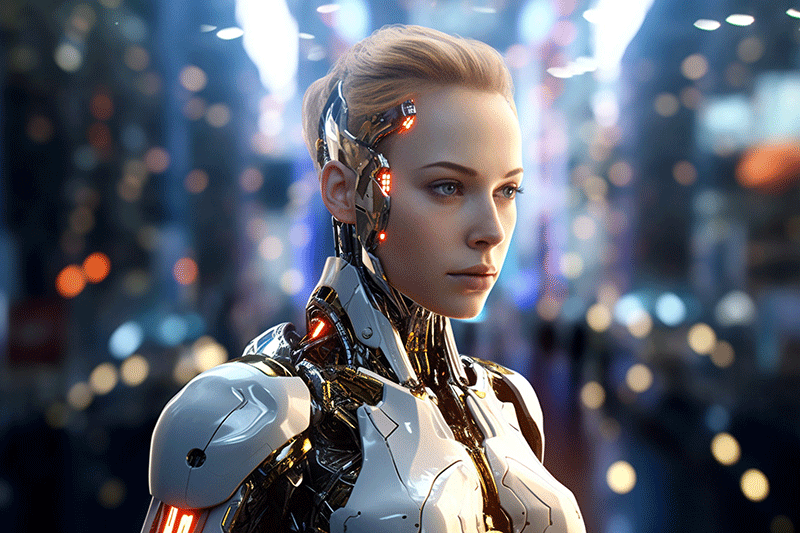
相关研究表明,人工智能近年来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动因主要得益于三个层面:并行计算(新型芯片“图形处理单元( unit,简称GPU)”开启了神经网络运行速率倍增的可能性)、大数据(数十年搜索储存的巨量数据成果用丰富有效的训练材料确保了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完善和提升)和更深层次算法(从数学层面上优化待处理数据中的元素组合结果,从而使数字神经网络质变性地加快了数据认知分析速度)。但是,这些技术上的提升并没有使人工智能从本质上摆脱技术范畴;也就是说,作为一门技术,它的屡次提升都限定于自身某一特定领域——换句话说,即使上述三个层面动因催化其发展,它还无法以足够的主体性意识到这一点,更不用说跳脱出来,审视人工智能科技整个领域与反思自己。一句话,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目前的人工智能具备足够能力来产生自主意识,这就决定了它是人工智能而不是人工智慧——而拥有自身意识的人工智慧是否属于人工智能的“终极愿景”,还是个众说纷纭的争议问题。
然而,开始涉足艺术创作领域的人工智能,包括项目本月“创作”的90秒钢琴曲,里程碑式地将人工智能往人工智慧方向推进了一大步。至于这一推进触及的是光明之门,还是潘多拉盒盖,探究将变得极其复杂;在笔者看来,它将至少带给我们涉及本体论以及艺术哲学层面的思考,这些思考不但会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关于艺术创作与接受的固有观念,甚至会触及人之为人的意义和尊严问题。
于是,在人工智能逐渐触达人类生活各领域,并以良好的技术素养带来优越表现时,长期以来有一种关注上述问题的声音显得固执而略带怆然:艺术将成为人工智能所无法触及的最后一片孤岛。时至今日,当人工智能开始染指作曲领域时,“孤岛论”还站得住脚吗?
对这一疑问的不同回答将是不同艺术本体观的体现。坚持以人文主义立场维护艺术创造尊严的人,通常会以人类先天不可替代的“第一性”主观能动特征,对制造机器的人无时无刻不在稳握并操纵技术这个立场加以辩护;另一方面,如果把目光放得更宽更远,尝试融合20世纪后半叶后现代主义哲学及文本学思潮来解读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答案未必这么简单,相反,对这首90秒钢琴曲能否属于真正的艺术创造这个问题的探究,将让我们重新审视音乐创制的终极含义——大师们留下的那么多扣人心弦的名作,真的全然出于通常认知中“我手写我心”的“创造”吗?
从左至右依次为吉尔·德勒兹、罗兰·巴特、雅克·德里达
在这里让我们先来快速综览后现代哲学及文本学思潮提出的几个颠覆性观念(篇幅所限,加之不直接关联主题而无法详述;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作进一步探究):德里达( )的“延异”(la différance)说、德勒兹( )的“块茎理论”()以及罗兰·巴特( )的“作者之死”(La mort de l’)。综合概括来说,在这些颠覆传统认知思维方式的激进理论中,通常观念中作品意义的“创造者”——作者不再存在,因为文本的意义并不根据作者主观意愿产生,而是根据不断变化的上下文语境获得即时性生产;文本并不指向任何意义,相反只停留在自身语境内意义的不断产生、碰撞与延宕中,并通过非线性、非体系、充满不确定与偶然性的“互文”,产生遥相呼应的触碰与关联,换成俗话,这些理论就是把“天下文章一大抄”论证一番。他们认为,只要进入某个语言体系(这里指广义上的语言,包括声音、色彩、动作、材质等,而不是仅指书面或口头字符)并在其中表达,不管是否驯服于其规则形式,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创造”都是不存在的,因为作品文本(同样,这里的作品和文本都指涉其广义概念)永远处在不断的意义关联过程中,要找到一个真正的原创意义绝不可能。
站在这些理论基点上思考,很难不动摇传统观念里对音乐创作行为本质的认知;实际上,音乐作品中一些脍炙人口的“互文”早已是普遍现象,仅举一例: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第一乐章这般经典的主题完全是在“借鉴”莫扎特创作早期一首名不见经传的歌剧序曲主题基础上加以申发的——歌剧序曲中18世纪的淳朴田园风情走进19世纪规模宏大的交响曲,竟摇身变为革命者形象的光辉写照。可想而知,当许多似乎原创性强烈的音乐文本(不止旋律,还包括配器、对位和音色的选择),都能从前人的篇章中找到“有章可循”的意义延宕轨迹时,对作曲家们来说真正意义上的“独创”还有几分能站得住脚,恐怕还真是个问题——如果要探讨基于巨量既有数据的存储和分析的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所“创作”曲目的“独创性”,当然更应作如是观。
所以,一旦“绝对独创论”殿堂的某根廊柱发生了动摇,随之而来的问题就会是:有血有肉的人类作曲家根据他们的天才灵感创造音乐时,本质上难道竟然与计算机作曲时那种基于摄入-分析数据而“创作”的套路无异吗?这个问题的尖锐性在于,它开始质疑曾被视作天才与神迹的艺术创作的终极意义。很难说这一质疑对人文主义立场上关涉人类智慧的传统认知与信念秋毫无犯;站在人工智能已经染指音乐创作的当下审视这一质疑,尤其令人难堪。
在这里,笔者无力对质疑作出全面回答;但这一质疑的提出,恰好能够将我们带到本部分开头与上部分结尾那两个问题上——绕了一大圈后,是时候重新审视它们了——
1、融合当代音乐史视角来看,未来人工智能作曲在音乐学上应当往哪个方向拓展自身?
2、 人工智能作曲的意义所在以及我们是否需要、为何需要它?
上文已述,计算机作曲兴发之时,正是序列音乐在西方世界大行其道,并吸引了结构主义等哲学目光关注之日;如果我们愿意在艺术哲学意义上承认作曲工作具有技术本位性质,而不是依靠“神迹与灵感”,那么我们将更容易理解这一轨迹的契合,并且相信这一契合将会继续下去,无论作者是有血有肉的人类音乐家还是计算机或人工智能系统,这一技术本位不会变。至此问题来了:计算机作曲已借助各种算法研究与改善,和同样注重算法的序列音乐并行发展了多年,二者都绝对算不上容易入耳;但最新人工智能则从模拟人类主观情感波动这一不同角度切入,却显然在努力构建一种亲和悦耳、旨在模拟传达并自主生产人类情感的“抒情向”音乐——从音乐发展史角度来看,这种人工智能“浪漫乐派”(暂且名之)的存在意义与前景如何?这些音乐文本,多年后能像贝多芬、肖邦、舒曼等人类“浪漫乐派”经典作品那样,在音乐史上占一席之地吗?别忘了,德彪西在上世纪10年代尚且说过:“产生飞机的时代需要它自己的音乐。”而现在,这个人工智能都即将“成精”的时代,作曲界还需要一个“换汤不换药”的肖邦吗?
在笔者看来,如果“90秒钢琴曲”这种音乐在未来被视为一种独立风格加以发展,那么它就将是悬空脱离时代的。诚然,从科学技术层面来看,这是人类科学史上一个巨大突破;但是其产生的艺术文本跳脱出了音乐发展史主流风格线路,与20世纪之前的音乐风格遥相呼应,这导致它(请注意,不是指人工智能作曲这一事件,而是指所作音乐文本)没有也不会给当代音乐史带来更多新的东西。
当然,在人工智能“作曲家”的“处女作”诞生不满一个月的当下,我们没有必要抓着这一首作品吹毛求疵;毕竟它正处于其发展原点。但是,一个漫想般的展望或许值得。在笔者看来,人工智能“浪漫乐派”那些悦耳的音乐(在可预见的将来,应该会越来越多)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它们将帮助人工智能系统获得更多人类情感认知与运作,其价值集中表现为工具价值。
设想有朝一日,当一套十分成熟的人工智慧作曲系统得以产生,其自主意识极有可能突破现有的“生产运作如人类般情感”的作曲理念时,恐怕它将不难借助巨量数据的存储与运作能力,以纵观音乐发展史的视角,以及对当下人类境遇与人性演进的审视与反思,创作出能够完全融入包含巴赫、贝多芬、瓦格纳、马勒、勋伯格等在内千年音乐史的音乐作品——也许到那时,这些人工智能谱写的音乐文本将和人类作曲家的作品并存,人工智能音乐也将成为一种新的、在人类音乐史上不可或缺的音乐流派。毫无疑问,在现在看来,这简直是个神话;但谁又能预见并勾划人工智能在作曲工作上的智慧上限呢?
只有一点是肯定的,诞生未满一个月的人工智能作曲,无论朝哪个方向拓展自身,都和人工智能技术本身一样。其存在的最大意义或许将在于 ——为我们带来更多关于自身的重新审视与思考,从而——在诸如“绝对的独创是否可能”、“艺术创造的终极意义”等恐怕永无定解的问题上——让我们更深入地发现自己。
— THE END—
触达「DT时代」热点,解读「数字传播」密码 。

